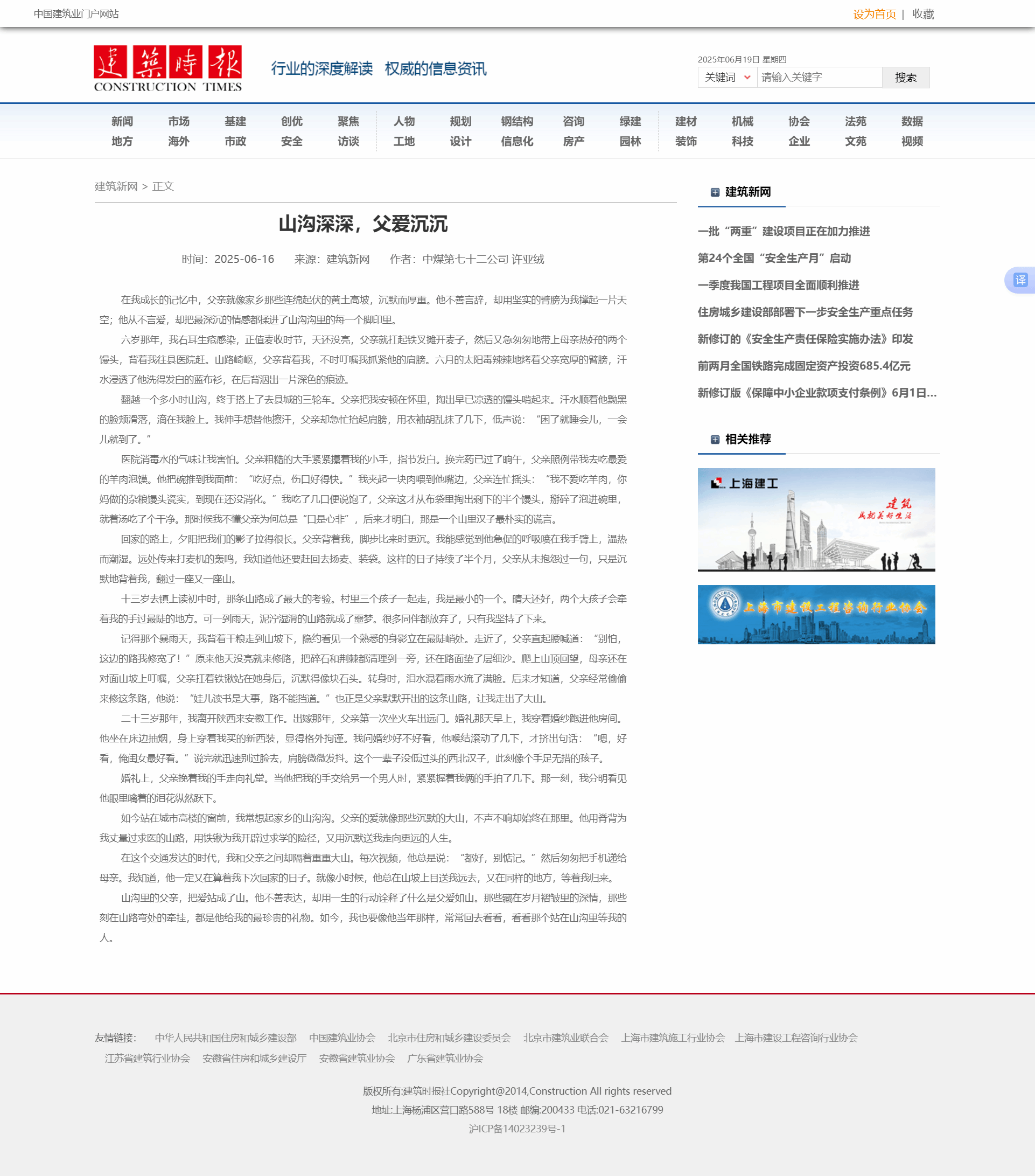
在我成长的记忆中,父亲就像家乡那些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坡,沉默而厚重。他不善言辞,却用坚实的臂膀为我撑起一片天空;他从不言爱,却把最深沉的情感都揉进了山沟沟里的每一个脚印里。
六岁那年,我右耳生疮感染,正值麦收时节,天还没亮,父亲就扛起铁叉摊开麦子,然后又急匆匆地带上母亲热好的两个馒头,背着我往县医院赶。山路崎岖,父亲背着我,不时叮嘱我抓紧他的肩膀。六月的太阳毒辣辣地烤着父亲宽厚的臂膀,汗水浸透了他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在后背洇出一片深色的痕迹。
翻越一个多小时山沟,终于搭上了去县城的三轮车。父亲把我安顿在怀里,掏出早已凉透的馒头啃起来。汗水顺着他黝黑的脸颊滑落,滴在我脸上。我伸手想替他擦汗,父亲却急忙抬起肩膀,用衣袖胡乱抹了几下,低声说:“困了就睡会儿,一会儿就到了。”
医院消毒水的气味让我害怕。父亲粗糙的大手紧紧攥着我的小手,指节发白。换完药已过了晌午,父亲照例带我去吃最爱的羊肉泡馍。他把碗推到我面前:“吃好点,伤口好得快。”我夹起一块肉喂到他嘴边,父亲连忙摇头:“我不爱吃羊肉,你妈做的杂粮馒头瓷实,到现在还没消化。”我吃了几口便说饱了,父亲这才从布袋里掏出剩下的半个馒头,掰碎了泡进碗里,就着汤吃了个干净。那时候我不懂父亲为何总是“口是心非”,后来才明白,那是一个山里汉子最朴实的谎言。
回家的路上,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父亲背着我,脚步比来时更沉。我能感觉到他急促的呼吸喷在我手臂上,温热而潮湿。远处传来打麦机的轰鸣,我知道他还要赶回去扬麦、装袋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个月,父亲从未抱怨过一句,只是沉默地背着我,翻过一座又一座山。
十三岁去镇上读初中时,那条山路成了最大的考验。村里三个孩子一起走,我是最小的一个。晴天还好,两个大孩子会牵着我的手过最陡的地方。可一到雨天,泥泞湿滑的山路就成了噩梦。很多同伴都放弃了,只有我坚持了下来。
记得那个暴雨天,我背着干粮走到山坡下,隐约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立在最陡峭处。走近了,父亲直起腰喊道:“别怕,这边的路我修宽了!”原来他天没亮就来修路,把碎石和荆棘都清理到一旁,还在路面垫了层细沙。爬上山顶回望,母亲还在对面山坡上叮嘱,父亲扛着铁锹站在她身后,沉默得像块石头。转身时,泪水混着雨水流了满脸。后来才知道,父亲经常偷偷来修这条路,他说:“娃儿读书是大事,路不能挡道。”也正是父亲默默开出的这条山路,让我走出了大山。
二十三岁那年,我离开陕西来安徽工作。出嫁那年,父亲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。婚礼那天早上,我穿着婚纱跑进他房间。他坐在床边抽烟,身上穿着我买的新西装,显得格外拘谨。我问婚纱好不好看,他喉结滚动了几下,才挤出句话:“嗯,好看,俺闺女最好看。”说完就迅速别过脸去,肩膀微微发抖。这个一辈子没低过头的西北汉子,此刻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。
婚礼上,父亲挽着我的手走向礼堂。当他把我的手交给另一个男人时,紧紧握着我俩的手拍了几下。那一刻,我分明看见他眼里噙着的泪花潸然落下。
如今站在城市高楼的窗前,我常想起家乡的山沟沟。父亲的爱就像那些沉默的大山,不声不响却始终在那里。他用脊背为我丈量过求医的山路,用铁锹为我开辟过求学的险径,又用沉默送我走向更远的人生。
在这个交通发达的时代,我和父亲之间却隔着重重大山。每次视频,他总是说:“都好,别惦记。”然后匆匆把手机递给母亲。我知道,他一定又在算着我下次回家的日子。就像小时候,他总在山坡上目送我远去,又在同样的地方,等着我归来。
山沟里的父亲,把爱站成了山。他不善表达,却用一生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父爱如山。那些藏在岁月褶皱里的深情,那些刻在山路弯处的牵挂,都是他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。如今,我也要像他当年那样,常常回去看看,看看那个站在山沟里等我的人。
 热点新闻
热点新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