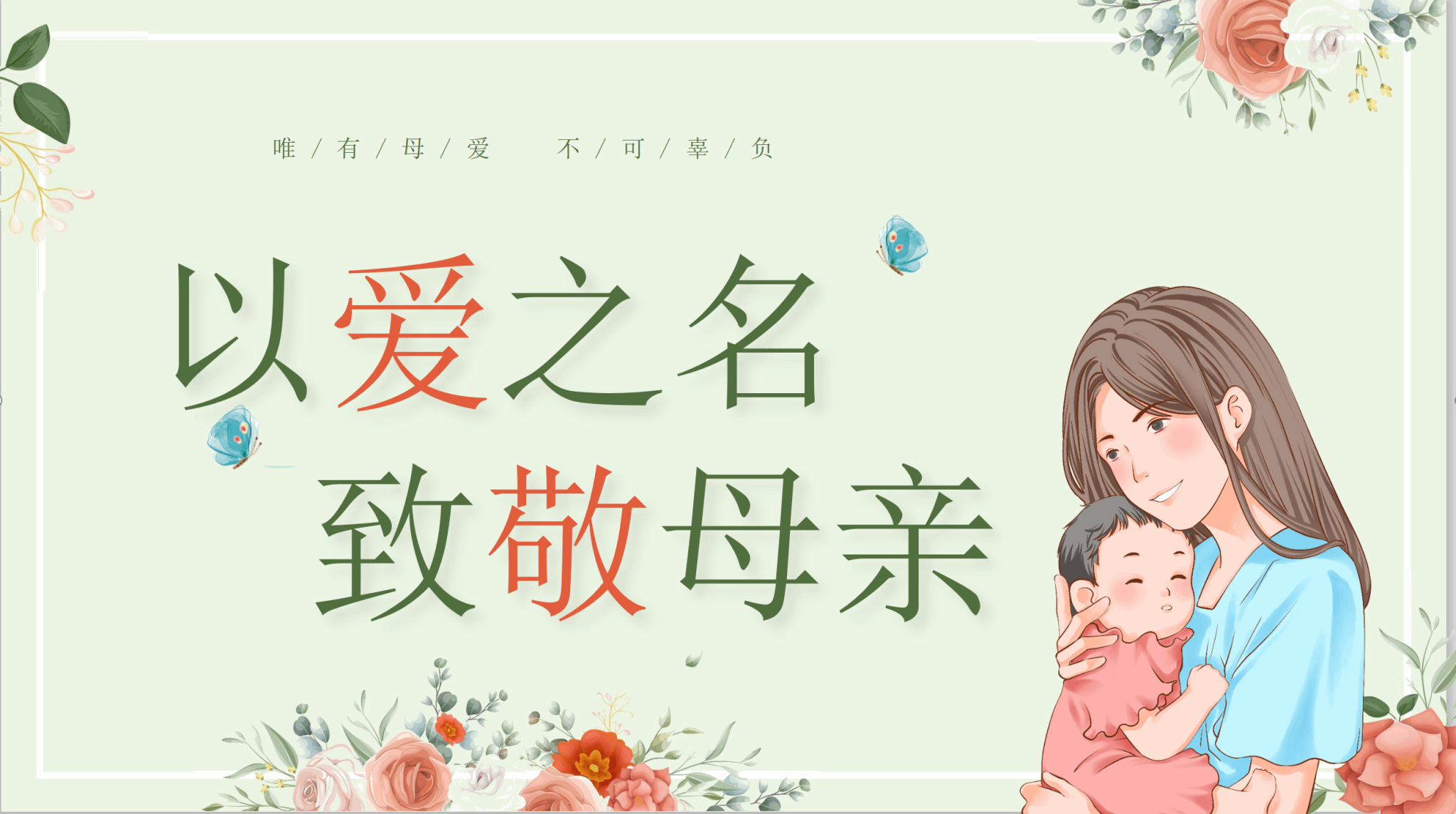
菜地里的油菜花又开了。
我蹲在我母亲的菜园地边,指尖抚过那抹嫩黄的花瓣,忽然想起母亲总说,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闻油菜花的香味。那时候她总穿着蓝布衫,扎两条乌亮亮的麻花辫,在村头的草甸子用木棒捶打晒干后的油菜杆,帮姥爷收获油菜籽。后来我在网络里偶然读到“春风起处阡陌老,万顷鎏绣流年”,才知道这绵延千年的农耕史诗,早已将油菜花的基因编织进华夏大地的经纬,更是中国人藏在血脉里的乡愁。
煤油灯畔的针脚。记忆里的夏夜总带着煤油灯的味道。母亲坐在堂屋的竹椅上,就着一盏摇曳的灯油光纳鞋底。她的影子被拉得老长,投在土墙上晃啊晃,像一只振翅欲飞的蝶。我趴在她膝头打盹,听着竹篾穿过粗布的"嗤啦"声,偶尔抬头,能看见她额角的汗珠顺着下颌滚进衣领,在月光里划出银亮的弧线。
“妈,你不累吗?”我迷迷糊糊地问。“不累。”她头也不抬,指尖灵巧地绕过针尾,“等你穿上新鞋,就能去县城里念好书了。”
那些夜晚的星光都渗进了她的针脚。当我第一次穿着千层底的布鞋踩在教室的水泥地上,分明听见鞋底的纹路里藏着无数个夏夜的风声。后来我才知道,她总在我睡下后摸黑做工,为了省灯油,常常借着窗棂漏进的月光穿针引线。有次我半夜醒来,看见她举着针凑近油灯,火苗在她瞳孔里跳动,把眼尾的细纹都照得清清楚楚——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,母亲的眼睛里盛着比星光更温柔的火焰。
米缸里的春天。老家的土灶台上,永远摆着一口釉色斑驳的米缸。小时候家里穷,米缸常常见底。母亲却像变戏法似的,总能让粗茶淡饭开出花来。她会把最后一把米煮成稠稠的粥,撒上把野葱花,让整个屋子都飘着暖香;或是把红薯切成细丁,和着玉米面蒸成窝头,在灶台的蒸汽里,那些粗糙的食材都变得活色生香。
最难忘的是有年春荒,家里只剩半缸陈米。母亲却瞒着我,每天清晨偷偷抓一把米藏在围裙兜里。直到有天我跟着她去田间,看见她蹲在田埂上,把米撒给一群呱呱叫的小鸡。“这些小家伙长大了,就能给你下蛋补身子。”她搓掉手上的米屑,指尖还沾着几粒金黄的谷子,“咱们人啊,就得像这土地一样,舍得把好东西埋下去,才会有盼头。”
那些被母亲藏进围裙的米粒,后来都变成了我饭盒里的咸鸡蛋。当我在县城的中学食堂打开铝制饭盒,咸香的气息漫出来,我忽然明白,母亲的爱从来不是汹涌的江河,而是地下的暗流,在看不见的地方默默滋养着生命的根系。
电话里的月光。刚参加工作那会,母亲总能算准我休息的时间打电话给我。“吃饭了吗?”她的声音带着电流的沙沙声,却比任何旋律都动听,“我今天蒸了你爱吃的花卷,面发得可好了,松软得能攥出水来。过几天休息了别忘了回家来吃。”
有次下暴雨,我单位的办公室里坐着,听着雷声发呆,电话突然响了。母亲的声音里混着哗哗的雨声:“我刚收完院子里的衣服,怕你惦记家里。”后来我才知道,那天她冒雨冲出去收衣服,摔在泥水里,膝盖肿了好几天。可她在电话里只字未提,只反复叮嘱我“别冻着,多喝热水”。
去年冬天,我在加班后给她打电话。她接起时背景很静,我听见老式座钟的滴答声,还有她轻微的喘息。“妈,你还没睡?”
“没呢,”她轻声说,“等你电话呢。”
我抬头看窗外,月光正静静地铺在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。忽然想起儿时停电的夜晚,母亲总会点燃一支蜡烛,放在窗台边。原来这么多年,她一直是我生命里那盏永不熄灭的烛火,在每个等待的夜晚,把月光酿成温柔的牵挂。
白发里的银河。上个月回家,母亲正在菜园里择菜。阳光穿过栅栏架的缝隙,落在她的发间。我这才惊觉,母亲的头发不知何时已白了大半,银丝在风里轻轻颤动,像落在青石板上的月光。她抬头看见我,笑出满脸的褶子:“来得正好,一会带点青菜回家,你看这菜多新鲜。”
我蹲下来帮她择菜,触到她手背的皮肤——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啊,掌心的茧子比往年更厚,手指关节微微变形,却依然灵巧地掐断豆角的茎。“妈,我给你买了护手霜,你看你这手,都干成啥样了。”我掏出包里的护手霜拧开盖子帮母亲涂抹在手上,母亲的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。
当乳白的膏体渗进她的掌纹,我忽然看见那些深浅不一的纹路里,藏着无数个日夜的烟火:有抱着我哄睡时轻拍的节奏,有在灶台前颠勺的弧度,有牵着我走过青石板路的温度。“小时候总盼着你长大,”她忽然说,“现在才知道,孩子飞得再远,妈这心里啊,还系着一根细细的线。”
暮色漫上来时,我们坐在园地里。母亲指着天上的星星,说起我小时候总把北斗七星认成勺子的事。她的声音渐渐低下去,像一片落在水面的叶子。我转头看她,发现她的睫毛上沾着亮晶晶的东西,在星光里微微发颤——那是母亲藏了一辈子的眼泪,只在无人的时候,才敢落进岁月的深潭。
油菜花又开了。此刻我握着那朵油菜花,花瓣上还凝着清晨的露水。原来母亲就是我生命里的油菜花,把所有的苦都酿成收获的甜,把所有的累都藏进了笑。那些被她抚摸过的岁月,都带着阳光晒过的温暖气息;那些她走过的路,都在我脚下延伸成温柔的河床。
风起时,油菜花轻轻摇曳。我忽然想起诗经里的句子:“凯风自南,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,母氏劬劳。”原来千年之前的诗人,早已写尽了天下母亲的心事——她们是南风里的柔风,是棘丛中的暖光,是岁月长河里永不褪色的温柔掌纹。
手机在口袋里震动,是母亲发来的消息:“晚饭做了红烧肉,早点回来。”我看着屏幕上的字,忽然湿了眼眶。原来最深的爱从来不在惊天动地的誓言里,而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,在每个等待的黄昏里,在油菜花年年盛开的菜园里,在母亲永远为我留着的一盏灯里。
菜园里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,我把油菜花捻在手指间,向家的方向走去。暮色中的老屋越来越近,母亲的身影已在门前晃动,像一株永远向着阳光生长的植物。而我知道,无论走多远,我的根永远扎在她的目光里,我的心永远盛着她给的春天。
这人间最动人的故事,从来都藏在母亲的白发里,藏在她眼角的皱纹里,藏在每个平凡却温暖的日子里——那是永不凋零的油菜花,是刻进生命的年轮,是我们永远的来处与归程。
 热点新闻
热点新闻